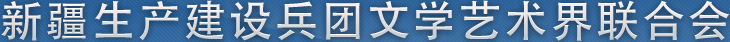同学肖刚
肖刚是我初中同学。我的初中是在6连上的。团部中学太远,连队住得分散,团里就在6连又办一所初中。片区内适龄学生就到了6连上初中。说是一个片区,连队之间相隔都远,肖刚家的2队离6连就有10公里,我家的9连还往2队延伸下去6公里。我们都住校,周六下午回家,周日下午又返回学校。
肖刚学习不好,各门功课都不好。我有时问他:你咋回事,上课也认真听着呢,咋就不懂?肖刚对自己很恼火,就拉个脸,冲我吼:我怎么回事,你说我怎么回事!看起来是对我发火,其实是生自己气。
有一次暑假,我去伊犁表哥家玩,晚回校个把月,到了班上发现数学课本已学了小半本。我问肖刚,前面数学怎么做。我记得是三角函数。肖刚很认真给我讲解,从他的讲解中,我发现他还是没有学懂。我就自己看书。大约一星期后,我就跟上了,而且又走到全班前几名。肖刚还是原地踏步,每门功课都在半懂半不懂之间。他抓住我领子:怎么搞的,怎么搞的,你是怎么学的?他不用“咋”这个词,他用“怎么”这个词,即使恼怒时也这样。我们新疆长大的孩子,语言结构、发音有很重的地方特点,比如:“很好”,我们说“好得很”,“干什么”,说“干啥呢”,“啥”还不念“sha”,念”sa”;“怎么回事”,说“咋回事”。等等。肖刚说话不同,尽管也是一口河南腔,但用语结构、特点是不一样的。
我是城里长大的孩子,才随父母下放团场,所以连河南口音也没有。我刚接触肖刚,就觉得他另类,还不止说话方式,他的衣着、行为、生活习惯,都与老团场孩子不一样,显得讲究。也许习性接近,宿舍10个人,我和肖刚走得近,去教室路上、去食堂打饭我俩都一起,周末回家也经常一起走。我俩个头、肥瘦相当,都是一身黄军装、黄军帽,而且洗得干干净净,连里人以为这两个形影不离的孩子,是一对亲兄弟。
一次周末我俩结伴回家,走到2队他到家了,我还要继续往9连我家赶。他说去我家坐坐,喝碗水再走。我看日头还高,就去了他家。一排低矮平房,屋檐搭的苇草,我手伸直就能够到。我跟在肖刚身后下几个台阶,进到他家。尽管有思想准备,一个普通农工的家会很简陋,但还使我吃惊不小。太简陋了,一间不足10平米的房间,全部家当就一张大床,一只小板凳。对了,墙角处还有一张桌子。我记得肖刚说过,他家5口人,除了父母还有一个姐姐一个弟弟。虽然姐姐已工作在其它连队,这么小的房子4口人也住不下呀。
但家里异常干净,床帮子、小板凳无一丝灰,土块垒的小茶几泥面光滑如板,硬质泥地面平整无尘。一般农工家我去过,邋遢得下脚地方都没有,手摸哪哪有灰。肖刚家的干净、整洁出我意料。
肖刚妈看到儿子同学来家,格外热情,让座又倒水。座就是那个木质小板凳,水没茶,就放糖,白砂糖放了厚厚一杯底。我知道,团场白砂糖像清油一样精贵,我妈每次炒菜,锅底只用缠了布的筷子头擦几下,而白砂糖我基本没见过。肖刚妈一下给我倒那么多,他家以后还过不过。
也许劳作中途回家喝口水,他爸回来了。他爸中等个,微胖,拿掉草帽头发显得稀少。他爸见到我不吭声,只略微点一下头,算是打招呼,然后坐床上喝水。房间太小了,几个人坐那几乎就是面贴面,哈气都能闻到。我就起身走到桌前,趴在桌沿上看墙上两个并排挂的镜框。镜框里镶满了黑白照片,有家里人在团场的留影,更多是他爸妈在城里的照片。他爸穿一身白色公安制服,或站或坐,有些气度不凡。我看了一会,觉得时候不早,就一人回9连了。
回到学校我问肖刚:你爸以前是干什么的?肖刚一脸失落,低头不看我,说他们家以前在北京,就住前门附近,他爸是北京市公安局的民警。肖刚七八岁时,他爸被判刑发配到新疆,他妈领着姊妹几个跟着也来了。肖刚说着眼里噙了些泪水,头勾得更低了,说他爸现在还没刑满。我一时不知说什么好,觉得这里的情况咋那么复杂。
后来我才知道,连和队是有区别的。连里的都是团场正式职工,或刑满释放人员,叫新生人员。队里的则是正在服刑人员,白天干活是用枪押着的。肖刚的父亲就是属于这一类。
初中毕业那年,我父亲落实政策回城了,我也跟着回城了。
有一年,我在城里广播电台做编辑,一天一个小伙子找我,一进门就问:安江友在吗?一口河南腔。我说你找谁?小伙子说:我找安江友。我说我们这没这个人。小伙子从兜里拿出一张纸,看着纸说:是安江友。我一下反应过来,说就是我,就是我。马上站起来给他让座。我姓秦,这肯定是哪个朋友只写了我的名,姓省略了,友就是朋友嘛。我说你是……他说我是肖刚的弟弟,我哥让我来看你。随手把一篮鸡蛋放到桌上。我问你哥怎么不来?他说他哥整天在地里干活,没时间。
前几年一次同学聚会见过肖刚,也许时间久了,也许人多,见面时他并没表现出多少热情,我也多与那些活跃同学应酬,没顾上与他多谈,只知他在团场一家修理厂工作。肖刚与我同岁,现都是50好几的人。不知他父母现还在不在,抑或依然住在团场?
连队小学
1970年6月19日,我家下放农场。一早,一辆解放牌汽车拉着我家6口人和全部家当,从乌鲁木齐向沙门子农场进发。路程虽200多公里,可驾驶员不熟悉路,当晚住在了下野地,第二天上午才到达团部。一个干部模样的人,从一栋平房里走出,在一个本子上看了看,指着一个方向说:沿这条路走下去,见到连队就到了。汽车在沙包窝里开始兜圈子,一会左拐绕过沙包,一会右拐绕过沙梁,一个多小时后,车停在一片地窝子前。一个戴草帽的人走来,与我爸交谈几句,车就开到一座新地窝子前停下。所谓新地窝子,就是地下挖了大坑,然后放上几根木头,木头上盖上干草,草上糊上泥巴,就是房顶。草泥刚把房顶糊上,泥巴在中午的阳光下冒着湿气,没糊严的麦草从泥巴中一根根冒出,像旧棉衣里露出的烂棉絮。两三个天窗没来得及蒙上塑料薄膜,看过去是几个黑洞,像大石块砸
出的深坑。
我爸沮丧,不愿多说一句话,我妈双手捂脸坐在车上哭。我们孩子却觉新鲜,来到一望无际、满目黄沙的野地,一个全新的世界。这时有三三两两人来看我们。他们也是刚从城里来到这里。天近黄昏,我们下土台阶,把家搬进了地窝子。
晚上,我躺在地窝子的床上,透过天窗望到一孔深远的星星,星星们非常明亮,像从我家天窗口射出去的满天礼花。看得久了,又感到星星很近,因为夜晚只有它们与我交流。
到了第三天,我们就去上学。学校离连部有2里路,是过去老连部废弃的地窝子。三、五年级一个教室,二、四年级一个教室。我继续上我的五年级。老师是一个江苏知青,姓管,我们叫他管老师。管老师一进教室,先让五年级学生做作业,然后教三年级新课。教完三年级,再教五年级。说是一个年级,也就五六个学生,两个年级加起来,也就10来人。电影《凤凰琴》里的山村小学,条件比我们好,他们还有土坯房,木制桌凳。我们的课桌是用土块垒起,上面搭块木板,课椅是从家里带来的小板凳。
只有语文数学两门课,管老师教完语文再教数学。我的地理概念很差,历史知识贫乏,大概和那时的教育有关。
每到星期天,我们就结伴去沙包里打柴火。有些柴火随手可以捡到,有些得用坎土曼挖,斧头砍,还得用脚踹。开始我只能背一点点柴火,还不如一个女生。因为柴火突兀得硬枝扎背,我就学他们垫上厚厚的绒草。那样虽然背得多点,但也永远赶不上当地随便一个男孩子。
最盼望下雨,雨水一来,教室成了一水坑,我们就可放假。冬天柴火连里供不急,就得停课,没有火炉的地窝子,冻得死人。夏忙时得跟农工一起下地,给棉花定苗、打顶、脱裤子,秋收要到地里拾棉花。拾棉花是个缠人的活,头遍花9月拾,二遍花10月拾,三遍花就是霜后花。打了霜的花,卖不出好价钱。翻过年到了春节,又天天晚上围在火炉旁,陪着父母剥棉桃。经常大年三十晚上,边吃年饭边剥棉桃,直到开春,又一年春播开始。农工一年四季像伺候老佛爷一样伺候棉花,修大渠、挖灌排渠、拉沙改土、积肥垫圈,力气全花在棉花上。凡从农场出去的人,再不愿回去,他们被棉花累怕了。
我一到连队小学,就成了娃娃头,带他们玩城里玩意儿:打髀什、赢三角、滚铁环、滑爬犁子。老师经常上课找不到人。一天早晨,管老师一进教室就宣布,全体同学放假回家,就把我一人留下。那天管老师站在讲台前,把坐在座位上的我一气骂了两小时,骂得我狗血喷头。大意是我带来了城里坏风气,不守纪律、不讲礼貌。坏风气就是那些好玩的玩意儿,不守纪律就是经常缺课,不讲礼貌是指称呼老师不带姓,比如叫管老师只叫老师,没有叫管老师。
那天我哭了,同时也记住了,叫老师一定要把姓带上。这个习惯我坚持了几十年,见到受尊重的人,称呼一定要带姓,比如王局长,赵主任,绝不再会犯低级错误。
上完五年级,我就到另一个连队去上初中,再也没见过管老师。听说管老师后来到团里当了协理员。
我的初中
我的初中是在6连上的。我家9连到6连有16公里路程,所以我的初中三年是住校读完的。住校就是周一至周五住在学校,周六下午回家,周日下午再返回学校。附近几个连队的适龄孩子,都住校。
6连是全团第一个开办初中班的连队,从初一办起。10人一间宿舍,教室在宿舍隔壁,是连队腾出的一间办公室。那年我刚满14岁,以前从未离开过父母,单独一人到了新地方,就没有了魂。自己拿碗筷到食堂打饭,自己洗衣服,不愿意天不亮就起床到几十米外的水井打水,于是早晨不洗脸刷牙是经常的。偶尔有人打来半盆水,10人的毛巾都伸进去,中午放学回来一看,半盆水已成泥汤。
第一学期,我没进入学生角色,忘记来6连干什么,整天恍惚,想家,神不守舍。听不懂老师讲什么,黑板上字母一个也念不出。我的脑子等于丢了。第一次数学单元测验,我考了0分,第二次考了5分。潘老师在班上讲评:秦安江有进步,这次考了5分。我不知羞耻,也不知潘老师讲的进步是什么意思,只是坐在座位上傻笑。但俞老师还是让我担任了初一班的班长。我不知他为什么会选中我做班长,学习不好,不会干农活,与人相处又没眼色。多年后我问俞老师,他说:你家是从城里下放来的,我也是城里下放来的,命运使然。
每天早晨天不亮,班主任俞老师就来到宿舍,把我们一个个从床上揪起,跟他跑早操。我们天天半闭着眼,拖拉双腿,在天边鱼肚白的微光下,围着连部跑圈圈,把好多职工都吵醒了。班里还种试验田,下午放学到地里除草、浇水、施肥,是我们经常要做的事。我们整天蓬头垢面,衣服脏乱,不像个学生,像外头乱跑没人管的野孩子。
初一上完,听说9连也要办初一,我找俞老师,说我要回9连再上一次初一。俞老师说你该上初二了。我说我想家。寒假期间,俞老师骑自行车去我家,找我父亲谈我的上学问题。俞老师走后,父亲说,你还是去6连上学吧,你的俞老师挺看重你。我不知俞老师非要我去6连上学是什么意思,既然父亲说了,那就去吧。因为我是一个听话的孩子。
从初二开始,我学习成绩一路飙升,成了班里尖子,也离开班长岗位,负责全校团小组工作。因为团支部在连里,学校只设团小组。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初一第二学期,我还不满15岁,俞老师就发展我入了团组织。当时学生中就发展了我一个,据说以后6连中学再也没发展过学生团员。
第一次召集团小组会,一间房子都是学校老师,我语无伦次,满脸通红。可老师们并不在意我的存在,只是相互吵架,一直吵到吃午饭时间。他们吵什么,我听不懂,也插不上话,只是谁说话我就望着谁的脸。过后我问俞老师,他们在争什么?俞老师说不管他们,那些破事与你无关。一个15岁的少年,第一次接触了大人们之间的是是非非。
从初一下半年开始,俞老师就领着我班全体十几个学生打土块,盖教室。一年盖一幢,初中三年下来,校园里就盖起了三幢教室,我们升到初三后,下面的初一初二学生,就都坐在新教室里上课了。
打土块是一件力气活。3块坯的模子,一个少年端起它来不容易,一天要端100下,倒出300块土块,才算完成任务,而且挖土、和泥、码摞、清场,都是自己。我体格瘦弱,俞老师就派一健壮女生与我搭伴帮我。一幢房子的土块打完,人就躺在床上再起不来了。那些天,我的手指是圈起来的,伸不开,一伸指关节嘎巴作响。腰直起弯不下,弯下直不起。腿和小腹一碰触,像被火烧似的疼痛。盖教室我们学生作小工,和泥、甩泥、挑泥桶、给脚手架上的大工扔土块……力气小的男生根本坚持不下来。
拾棉花是最磨人的活。中学生每年拾花任务很重,要在地里泡两个月,才能完成任务。天还黑着,人们就三三两两下到地里,弯腰曲腿开始拾花。中午饭地里吃,水有人挑到地头。开始几天,眼泡是肿的,腰是躬的,腿是疼的,手指被棉壳扎出一道道血口。晚上回到宿舍倒头就睡,还没睡醒,就又伴着星星下地。我拾花手慢,除从独山子下放来的笨人杨健,我拾花斤数每天都老末。有一天,我下定决心不垫底,快吃快喝,不拉不尿,从天黑拾到天黑,拾了55.5公斤。俞老师就着马灯在地头宣布成绩,大声表扬我,说我有了不起的进步。那天我感到晚风特别柔和。
俞老师是上海知青,比我大一轮。他的爱人文老师也是上海知青,与他同岁。当时他俩从团校过来,创办6连初中。不久俞老师当了6连学校校长,后来又回团校当校长,几年后当了团政委。我是在6连初中毕业后,随父母回到城里,在城里高一没上完,就参加了工作。
6连初中三年,是我学生生涯最正规的学习教育阶段,也是记忆最深刻时期。我的学生知识积累,基本从那里获得;我的价值观形成、校园记忆,也多是那里。俞老师和他的爱人文老师,我们多年一直保持联系。他们现已退休回到上海,过着晚年生活。俞老师天天钓鱼,当起了渔翁,文老师喜欢上摄影,她的作品经常在社区展出。他们的两个儿子,老鹰和文文,都在上海有一份很好的工作。他们已经抱上孙子了。
我的文体
我从小个矮体瘦,体育不是我的长项。班上打篮球,我只能在场外观战,蹦着跳着,喊得嗓子嘶哑。最多就是散场后,球员们走了,我跑到篮下一人抱个球投篮。一次比赛,场上少一人,让我顶上,我卖力地全场疯跑,就是抓不到球。突然一球传来,我正好在篮下,球从空中划着弧线飞向我,我伸出双臂站稳双腿,准备迎接球的到来。这时所有人都看到了,球呼啸着从空中落下,犹如一颗大口径炮弹,准确无误击中我怀,我被击得坐倒在地。那一瞬间,我听到人们的埋怨声,看到不屑的眼神。我恨不得钻入地底,不再见人。
田径我也不行,百米跑14秒,单杠翻不到杠上,山羊跳不过去。就连最普通的儿童游戏——斗鸡,也是谁都能把我斗倒。我煞有介事架起单腿,一蹦一跳冲向对手,人家一挑一压,我立即歇菜。每到上体育课我就自卑,觉得自己是一个最无能的人。
可是我乒乓球好。学校新垒了一个水泥面球桌,大家同时起步,一年后我就独领风骚,见谁打谁,坐在庄上不下来。俞老师是上海知青,从小有底子,发球姿势眼花缭乱。那次全校比赛,我和俞老师进入决赛,他发一球我扣死,发一球我扣死,最后大比分完胜。我终于在体育方面,拿了一项冠军。从那以后,我见了那些体育尖子,心里想的是:看把你们能的,拿拍子来,咱球台前试试!
文艺我也不行。首先没有好嗓子,声音沙哑,音域太窄,高音上不去,低音下不来。学校排节目,独唱领唱轮不到我,《红灯记》我演没一句台词的跳车人,《智取威虎山》我演站在边上只一句台词的申德华。许燕明什么都不行,就是天生一条好嗓子,每次排节目,他的独唱《我为祖国守大桥》《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总是倾倒一大片人,成为学校的时段红人。有时我对着镜子摸喉咙:我妈怎么生得我,这么一个破嗓子。
一次寒假在家,连里在地窝子礼堂组织文艺节目,职工们上台自演自乐。我和杨华合说了一段天津快板。那个节目是我从城里带去的,城里学校演出时,我非常喜欢,就偷偷学会记住了。演完节目回到家里,我妈高兴极了,摸着我的头,说我儿子还会演节目,真是了不起。眼睛里流露出的欣赏,让我非常享受。我的两个妹妹,也在我身边跳来跳去,说我哥的节目好看。
长大后,自知声音条件不好,就有意避开娱乐场所,卡拉OK、歌舞厅尽量不去。有时也憋不住,听到电视里的歌好听,也跟着哼哼。这时妻子就急,说别吵,让我听宋祖英唱歌。偶尔同学聚会,酒到酣处会唱几声,释放心中豪气。虽然我唱不好,但在酒精作用下,也唱。可一开口,我就能从别人眼中看到:他这唱得啥?若继续唱,就会有人干涉,说算了算了别唱了,换个人吧。这对我打击挺大,几次以后,对唱歌我就彻底闭声了。
但我天生是文艺爱好者,不会因某方面条件制约,就压抑天性的迸发。我学得了一手好二胡,也会拉小提琴。学校文艺汇演,工作后团里演出队,都有我悠扬的琴声。后来我到文艺部门工作,经常做艺术门类评委,每当评判声乐,我就说不出个子丑寅卯。有时我想,这辈子怎么就怕了声乐呢?人家腾格尔、韩磊也都是沙哑嗓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