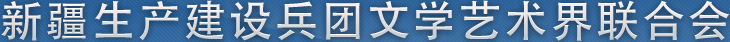没想到《草原之夜》歌咏的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垦荒战士的生活,没想到这支流传甚广的东方小夜曲是为一部名叫《绿色的原野》的影片而作,没想到歌中唱到的可克达拉是绿色原野的意思。没想到,2017年九月上旬,我有机会直观地比对一片荒野的前世与今生。
可克达拉的前世保存在画质轻微磨损的彩色纪录片里。荒滩、积雪、结冰的河面、吹得人站不稳的大风、用芦苇和泥土构筑的地窝子、从地窝子上呈S形艰难攀升的炊烟、一些睫毛结着冰碴子鼻孔喷着热气的伊犁马、许多因年轻而饱满因激情而灿烂的面孔……可克达拉在1959年左右的模样,由这些素材拼贴而成。
纪录片里大多是冬景,没有出现迷人的绿野,依我的观察和分析,有些反映当年劳动成果的镜头也并不是在可克达拉拍的,选取的是兵团其他较发达地区的景象。因此,“绿色的原野”这个片名,更像是一种隐喻和祝福:“等到千里雪消融,等到草原上送来春风,可克达拉改变了模样,姑娘就会来伴我的琴声。”
我喜欢这首歌的开头用琴声的悠扬和草原的空阔描绘的恬静,也爱它在结尾用春风和爱情传达的理想主义情绪。
片子看了一遍仍不停回放:骑马踏入冰河俯身用搪瓷缸舀水直接饮用的战士;各族战士生活和联欢的场景;晚霞映照时抱着琴思念远方的身影……电脑屏幕上的旧时光一闪一闪地喷溅在脸上,把我浇筑成神情专注的泥塑,一边研习纪录片,一边搜索导演兼《草原之夜》词作者张加毅、曲作者田歌的身世。他们是在采风时目睹垦荒战士弹琴唱歌的情景触发灵感而作。张加毅早已离世,田歌仍健在,不过据我了解,他们其他作品的影响力,还没有超越《草原之夜》的。张加毅的骨灰也洒在了可克达拉。
从伊宁前往72团时,在车上与同行者谈到我对这首老歌的偏爱,兵团文联的一位诗人说:这么好的歌,只有在充满激情的青年时代能写出来。
这个判断逻辑并不特别严密,但我深表赞同,有一种美与纯情,确实只可能是青春的产物。
这次的拜访对象却不是青春,是在荒野上耗尽了青春的老人。她们有的散坐在团场福利院的榆树下拉家常,有的啥也不干,盯着树荫中太阳的光斑打盹。在辛劳的鞣制和时间的浸泡下,她们的皮肤干涩布满深纹,枯白的发丝在下午的轻风中柔柔地飘举着,像无数细微的旗帜。
她们是第一代军垦战士的遗孀,自身也都是兵团人,大多来自湖南和山东,不少是“八千湘女入新疆”时来到可克达拉的,她们或她们的家人是不是在纪录片里出现过?本想提及这个话题,听了她们的自述,却觉得没有必要。
青春已远离面容,她们的话语方式仍停留在遥远的年代。因为牙齿不关风,也因为方言的局限,很难完全听懂她们的讲述,关键词却很清晰:很苦。不怕。感谢。
坐敞篷汽车吃着风沙从内地到新疆不苦。刚入伍时因个子太小扛不动枪急得直哭也不苦。住在低矮潮湿的地窝子得了关节炎不苦。同土匪和敌人打仗不怕。和沙漠、戈壁、荒地打仗更不怕。感谢的对象是党和兵团,让大家老有所养,过上了“过去的地主一样的好日子”(维吾尔族老战士阿瓦汗语)。
在63团拜访一群退伍海军战士时,听到的关键词也基本如此。他们因伊犁河航运开发奉调入疆,命令中途变更后,他们就地加入垦荒大军。从水最多的大海来到水最少的荒野,由开军舰的变成握锄头的,个人命运的修改无奈而突兀。他们不仅不诉苦,还总结出两句话表达对边疆的感情: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
在兵团四师和可克达拉的辖区跑了两天,没看见多少荒地,连接着每个团场和连队的,是亮黄的玉米、暗红的高粱、深绿的甜菜、褐白相间的棉花。它们以罕见的气势铺排着,没有山川和沟壑阻隔,每一处都像是在举行生长比赛,每种作物的每垄纵队,都可以一口气长到土地尽头与蓝天接壤。
可克达拉位于伊犁河谷中部,北有科古琴山抵挡西伯利亚的寒流,南有哈克他乌山防御塔克拉玛干沙漠的风沙,西有喇叭状缺口迎纳地中海和大西洋的暖湿气流,中部还有水量丰沛的伊犁河横穿而过,气候条件在新疆地区相对较好,适合瓜果贮存糖分,也适宜机械化农业。新疆的棉田不仅比南方面积大,还有矮、密、早的特点,棉株长得矮,种得密,成熟得早,远看像是绣在荒野上的巨幅地毯。
自伊宁往西20公里,见一处簇新的小城,高低错落的建筑刷着色彩鲜艳的墙面漆,远看像积木,近看是刚建成的住宅小区、办公楼和商场。有的阳台上晾晒了衣物,有的还在叮叮当当地装修。纵横交织的街道宽整得像飞机跑道,与飞机跑道不同的是,两侧迎宾似的站着白蜡树、榆树和槐树,有的是树苗,有的是移栽过来的成年树。
当地朋友说,我们到达的是2015年4月才成立的可克达拉市的市区,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立的第8座城市。它东临伊宁机场,西接霍尔果斯口岸和经济开发区,是新丝绸之路上的重镇。
这就是歌中憧憬的“改变了模样”的可克达拉吧。关于这座年轻边疆城市的轶闻很多,印象深的有两件:2017年初市区一新楼盘开售时,抢购的人提前20个小时来售楼部前排队,为了躲避夜间的寒冷,不少人把家里的棉被当大衣裹在身上。购房者不只来自可克达拉,还有伊宁和周边城市的,甚至有不少江苏人不远万里赶来。
另一件是,装扮市区的那些绿树中,有32000多棵是市民们无偿捐赠的。一位67岁的退休教师把40年前在自家门口栽下的17棵槐树全部捐了出来,每棵直径都在65厘米以上。把自家的树移栽到公共绿地上,这样的事我过去极少听说。
可克达拉的湿地公园里满目皆是苍翠的馒头柳、圆桂榆、国槐、白蜡树、红柳。在伊犁河畔,大片大片的芦苇随风起伏,涌荡出一些塞上江南的韵味。伊犁河不深,水也清澈,但流速很快,不时卷走岸边松软的沙土,伸手入水,寒气像小鱼一般飞速聚拢啄食指尖,江南的错觉瞬间被水波席卷而走。在我熟悉的江西,9月上旬的江河里还随处可见戏水纳凉的人。
挺想去找张加毅当年捕获灵感的原野,好客的当地人却把我们拉进了浓香扑鼻的酒厂。没想到伊力特这个著名品牌也是垦荒战士的作品,它的年龄也和兵团差不多。曾经有好些年,《人民文学》杂志封底上出现的就是它,一个戴毡帽的哈萨克族帅小伙骑在马背驰骋于金色的原野。在巨大的酒甑前,酒厂的朋友劝我们品尝刚流出来的原酒时说:这些酒是伊犁河谷的精华。
某天中午,同行的作家们在屋里和兵团战士座谈,我端着相机在门前的公共绿地拍植物。可克达拉人与内地人性情不同,连树也如此。在江南,柳树低矮而婀娜,在可克达拉却高大挺拔得像是伟男。杨树和榆树更是如此。
两个姑娘并肩斜倚在榆树下的长椅上低语,一个挺着大肚子,一个看上去像大学刚毕业不久。她们的话很疏,许久才对上一两句。整个院子只有她俩,其他都是树木花草,似乎她们正同院子里的寂静说话。
在可克达拉,我时刻能感受到这种庞大的寂静感,精神不充盈的人不容易适应这种自省式的寂静,再增加一点点就是孤独了。
两个年轻姑娘中一位是第三代兵团人,另一个是从甘肃考过来的公务员,她说,她的不少熟人是从河南、四川、山东等省来可克达拉工作的。
向她们打听可克达拉草原,她们答:可克达拉最美的不是草原啊。等明年六月份来看万亩薰衣草吧,我们这可是世界排名前二的薰衣草种植基地,和法国的普罗旺斯齐名呢。
曾在摄影作品里见识过普罗旺斯的紫色天堂,每年六月,可克达拉的表情会美成什么样子呢?这悬念让我离开可克达拉时,开始了怀念,也开始了向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