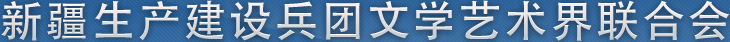《西长城》是一本关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书,书名后还有一个副标题:“新疆兵团一甲子”。新中国历史上,东西南北各个边疆都曾经有过生产建设兵团,但目前仅存的就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了,而且,转眼就是60年。
书的作者丰收是兵团二代,父亲曾经是黄埔军校的军人,1944年进疆之后就再也没有离开。丰收和写《白豆》的董立勃、写《英格力士》的王刚、写《老风口》的张者一样,都是出自兵团的著名作家,只不过他的创作以报告文学为主,作品有《绿太阳》《镇边将军张仲瀚》《西上天山的女人》等,都曾经产生过很大的反响。这一次的《西长城》讲述的是兵团六十年的历史,历史的主角是兵团的普通人。
兵团家史
《西长城》的序言中写道,解放战争打到1949年9月西宁解放的时候,以马步芳为首的西北“五马”撤聚新疆,打乱了中共中央建国后解放新疆的战略布局,于是派第一野战军彭德怀部抢占河西走廊 (当时的一野司令员为彭德怀,政治委员为习仲勋),切断“五马”聚合之路,然后派第二军挺进南疆,第六军挺进北疆。两军会师酒泉的第二天,国民党新疆省警备总司令陶峙岳通电起义,第三天,国民党新疆省政府主席包尔汉通电起义。(1983年,包尔汉快90岁的时候,写下了30万字的回忆录《新疆五十年》,王震作序,是了解新疆历史的必读书)
1949年12月17日,解放军驻疆部队、三区革命民族军、新疆起义部队会师迪化(乌鲁木齐的旧称),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新疆省人民政府同时宣告成立。之后,新疆开始剿匪平叛、建政维稳、筑路引水、屯垦戍边。
随着局势的平稳,中央决定部队除保留一个现役国防步兵师以外,绝大多数就地转业,“铸剑为犁”,在新疆落户从事农业生产。1954年10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正式成立,首任司令员正是率部队起义的陶峙岳。之后,兵团和新中国一起,经历了一段艰苦卓绝的岁月,全国人民都熟知的走西口、八千湘女上天山、十万上海知青进新疆、伊塔事件之后的“三代”戍边等都发生在这个期间。
而随着形势的变化,1975年兵团被撤销,改为新疆农垦局。198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联合发出《关于恢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决定》。《决定》指出:“生产兵团屯垦戍边,发展农垦事业,对于发展自治区各民族的经济、文化建设,防御霸权主义侵略,保卫祖国边疆,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1982年6月新疆建设兵团正式恢复,直至今天。
如今的新疆兵团有14个师,174个农牧团场,是“军政企合一的特殊社会组织”,遍布克孜勒苏以外的新疆全境,分布地区有37个少数民族。兵团的发展也开始从“屯垦戍边”向“建城戍边”转变。
“不到新疆,不知道中国之大”,在这片沙漠、戈壁、绿洲、山脉交相辉映的广袤土地上,兵团建设发展了60年,这其中有多少动人的故事、不朽的传奇可想而知。而《西长城》的作者丰收就像“兵团的荷马”,足迹遍布全疆,采访对象成百上千。最可贵的是,在整个书写的过程中,他也像写《荷马史诗》的无名诗人以作品为名流芳百世一样,从未露才扬己——在如此厚重丰沛的大历史面前,作者严格保持了一个修史者敬谨真诚的“无我”立场。为了这个立场,某些时候必须削句减辞,牺牲一些结构布局的合理性。
“飘荡新疆大地的种子,哪一粒都有一部人生传奇”
粗略说起来,《西长城》里的故事主角有几类:一是部队官兵,二是周总理说的“自动支边人员”,三是天山湘女,四是上海知青,实际上他们也是兵团的主要人员构成。而他们的故事,也是一个国家从战争状态走向和平岁月的全部反映。
战争是历史的极端状态,靠信仰、靠集体主义精神就可以激发不可思议的潜能,但和平岁月,需要面对的是吃喝拉撒、婚丧嫁娶的日常生活,单纯靠信仰、靠意志很难行之有效。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初创时期,正是处于两种状态的过渡阶段,信仰支撑下的集体主义精神仍旧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人本主义和人道主义的关怀也不可避免地提上日程,于是四类故事主角之间就发生了很多或悲或喜的人生传奇。
首先是部队官兵。书里讲到,王震的三五九旅进疆后变成了六师,进驻大芨芨草滩哈拉毛墩,一坎土曼(新疆的一种铁制农具,编者注)下去,见不着土,粮食成为首要问题。进疆部队20万,国家解决不了军粮的问题,除了自力更生,别无他法。王震说,驻守新疆,兵少了不够用,兵多了养不起,解决这个难题就是走南泥湾的道路!于是,昔日的战斗英雄变成了今日的种田能手。
书中讲到老兵李洪清,曾在毛泽东警卫连当过连长,是被聂荣臻元帅赞赏的著名的一一五师的“蛮子”排长。他参加过五次反围剿,走过二万五千里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大大小小的仗打了上百次,百团大战、平型关战役、淮海战役都有他的身影。他先后七次负伤,靠白求恩的无麻醉手术才保住右腿,获得过“八一勋章”、“独立自由勋章”、“解放奖章”。进疆之后,他是巴里巴盖草原的一名仓库保管员。在中国最需要粮食的1961年前后,巴里巴盖人给国家贡献了上百万斤粮食。
1981年,李洪清和王震在石河子重逢,他对司令员说:“攻打兰州时,你说,打不下兰州我要你的头,现在我的头还在。”看着书中照片上,昔日戎马的将军和士兵相对露出忠贞赤诚的笑容,会让人感叹激情燃烧的岁月从未离他们而去,而这种信仰和意志在角色转变过程中所发挥的凝聚人心的力量,如今看来,何其珍贵!
三五九旅唯一的一位知识分子团长、曾写下兵团史诗《老兵歌》的新疆军垦奠基人张仲瀚,用“十万大军出天山,且守边关且屯田。塞上风光无限好,何须争入玉门关”的豪迈诗句勉励官兵,也身体力行,亲自拾粪种田。他一生都在倡导的南泥湾精神真正融入了自己的血液、官兵的血液。而这种精神背后,是超出想象的苦难。《西长城》说:“十年、一百年,时间越久历史越长才越明白,他们的牺牲太大太大,他们的给予太多太多。”1980年,经历了“文革”苦难、无儿无女的张仲瀚在北京病逝,1993年他的骨灰随王震的骨灰重返天山。
新疆和田有一个四十七团的墓园,叫“三八线”,是以累死在田里的老兵周元开垦的长八百米、宽三百米的田命名的,而此时,恰逢朝鲜战争期间。客死北京的沈从文想念故乡凤凰,曾说:“一个士兵要不战死沙场,便是回到故乡。”天山脚下,有太多如此遥望故乡的老兵……
关于八千湘女,早已无需回避历史的真实。在被命名为《家国 女人》的第三卷,书里写到了来龙去脉。部队的婚姻问题战争年代就已经存在,扎根新疆,这个问题更是严峻:“没有老婆安不下心,没有儿子扎不下根”,于是,王震给自己的老搭档、湖南省委领导王首道写信求助:“在湖南招收大量女兵,十七八岁以上的未婚女青年,不论家庭出身好坏一律欢迎,要她们来新疆纺纱织布,生儿育女……”没几天,长沙的报纸天天有号外:新疆军区招聘团征召女兵!参军去新疆上俄文学校,开拖拉机,进工厂……随后湖南、山东、河南、四川、湖北、上海的女青年踊跃奔赴新疆……
太多的文学作品写到了湘女的眼泪,写到了时代对湘女的捉弄,《西长城》的作者也并未回避这一点,但除了这些有代表性的故事,他还找到了其他。比如他写到和刘少奇、何叔衡、谢觉哉齐名的革命家肖学泰的侄女肖业群,就因为在新疆找到了“根正苗红”的婚姻而受到了保护,免遭“文革”中的政治牵连。组织包办的婚姻在制造了很多悲剧的同时,也成就了很多喜剧,甚至护佑了很多人的命途。历史从来就不单一和绝对。
除此之外,作者还找到了大量的史料,包括入疆后女兵因理想和现实的巨大差距而发病的《癔病情况报告》,还有《部队五年来婚姻问题总结报告》等等。作为报告文学作家,他有更为宏阔的历史观:西部的爱情和婚姻也和所有地方的爱情和婚姻一样,有悲剧也有喜剧,有感天动地的忠贞和生死不渝的誓言。而且,人生终究不能纠结和沉湎于苦难,“悲剧前奏、喜剧谢幕的人生长剧”更该被人记住,也更是以“真善美”为宏旨的文学作品应该具有的历史品格和美学风范。
在历史转折的关键点上,一代人的命运应该被记取,但无法被改变。那些美丽的进疆女子和背井离乡的老兵一起,用青春谱写了一曲西部悲歌,当然也谱写了一种独一无二的西部血色浪漫。
关于上海知青,问题显然更复杂。它不是一时一地的问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全国性的,因而遗留的问题也是全国性的。与鱼珊玲(上海支边青年。六十年代初,不顾家人反对,拒绝去香港,报名建设边疆)同为知青典型人物的杨永青出身书香门第,但她们都积极投身时代潮流,奔赴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建功立业。作者说:“对于热血青年,古往今来都是一样,血亲的力量在时代潮流面前苍白无力。”只是,在特定的历史阶段,血亲也往往会成为她们命运转折的理由。那时候的中国,“唯出身论”制造了多少历史的悲剧!
杨永青说:“谁也超越不了时代。”如今看来,没有进疆的老兵、湘女、“盲流”,就不会有新疆的今天,而没有上海知青,兵团的教育也不会有后来的发展和改变。“时代导向他们的人生,她们也雾里看花云中望月地影响时代。历史是一场风云际会,愿意也罢,不愿意也罢,都会裹着你往前走。沧桑世事,潮汐人生,看世事还是看人生,她们都有了过来人的淡然恬静。”
人生朝露,艺术千秋,当《西长城》挥笔写下他们的故事的时候,他们的淡然恬静早已化为一种铅华尽洗的境界。而这种境界又反过来直接影响了《西长城》的语言风格,回顾故事的时候平实家常,甚至略显絮烦,但评点人生的时候意气平而旨趣深。
“人的喜怒哀乐往往是最真实的历史”
如果书是有气质的,那么《西长城》是一本冲淡平和的书。面对历史、面对苦难、面对太多人的命运传奇,甚至面对成绩,这本书都没有表现得煞有介事。曾经,一些主旋律题材的报告文学有过这样的弊病,即为了弘扬正确的价值观而一味增加文本的教化作用而不是感动功能,于是原本具有质感的故事变得空洞,原本可亲可感的人物也变得概念化了。实现文学的真实,不管是小说的还是报告文学的,都有一个技术手段或者说语言方式上的要求,那就是恰如其分、适可而止。《文心雕龙》所谓:“夸而有节、饰而不诬”,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但《西长城》又不是一味地书写平面化的“感动中国”的故事,它注重故事和细节的意味深长,擅长在历史的缝隙中,在超越时代局限的人之常情中展现写作者的智慧。在整体“无我”的写作格调中,那个充满洞察力和反省精神的“我”又会适时出现。当然,跟整体风格相匹配,“有我”的时候也是中正持重的。
书中写,兵团人荣誉感极强,战争中培养起来的集体主义荣誉感是兵团人的精神底色。其中连续八年的“万斤拾花能手”朱桂达的故事让人印象深刻。她几乎年年是先进,立了两次三等功,1980年就被评上了全国三八红旗手。但同时,她的身体也每每达到极限,“白天在地里硬撑一天,晚上回到家动都不想动一下……”奖状得了一大摞,到头来落了一身病。
她对采访她的记者说:“这些年,师里、团里的首长常来看我,鼓励我好好干。我感谢他们的关心。可是,他们每次都问我:今年生产怎么样?从来没有人问我:你现在身体怎么样?……我是个人,不是块铁。拖拉机是铁的,也要保养,也会报废……”“但话是这样说,工作还得干,谁叫我是个共产党员、劳模呢?”如此质朴和真实的表达,胜过所有文学的渲染。
也许是因为作者采访了太多一线的劳动者,知道了太多命运无常和人生无奈,也见识了太多无名者的坚忍和牺牲,他的笔下没有知识分子通常所具有的那种抽象的忧思,而是充满了“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朴实的“人民性”。
书中极为珍贵的还有写到了真实的边防生活。那时候的新疆,不可回避的就是和苏联的关系。在两国关系友好的阶段,苏联专家在种棉技术、饮水工程等方面给了新疆太多的帮助;而上世纪六十年代中苏关系紧张的时候,兵团战士又不得不代替边民在边境承担了“三代”的任务(代耕、代牧、代管)。书中写:“只要你去过边境,你就可以看到兵团战士把庄稼一直种到了边境地最前沿;有些地方甚至种到了苏军的铁丝网前……”“只有在边境上,才能认识每一寸国土的神圣。”“屯垦戍边”只有在这里才变得最形象而具体,读者也只有读到此处,才最能明白作者为何会把一本关于建设兵团历史的书命名为“西长城”。
“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文心雕龙》),朱桂达这样的劳模,总是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而不是一尊信仰的雕塑站在文本当中;兵团战士所处的这样的情境,也总是作为活生生的边防场景,而不是抽象的爱国主义信念站在文本当中。自然,这些才能够润物无声地走进时下读者的心里。
除了超出生理极限的劳动,兵团人也有文化的需求。书中并没有忽视这一点,最为令人动容的,是一个叫李慧的母亲。她是北京人,抗战时期的流亡学生,嫁的丈夫也是流亡学生。丈夫是一介书生,愤世嫉俗,新疆解放后进入学习队、后来又进了劳改队,最终生不见人死不见尸。带着两个孩子的李慧因此被一而再地劳动下放,地方越来越偏远,但即便如此,她还是从北京给两个孩子背回来两把小提琴。书中说,在母亲心里,喜欢小提琴不只是爱好而已,“这是儿子的生活态度”。事实上也是,她的孩子“无论多么困顿,只要自己有生命力,春天来临就一定会发芽”。
一个母亲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中国,用背着两把小提琴的背影支撑了贫乏生活中的丰盈人格,而无数的母亲则支撑了新疆兵团的过去和未来。作者说:“当我的视野里有了更多母亲,当我面对时代背景下她们的命运,思考人生的沉重,人性的依存时,我也思考着社会文明因牺牲而有的推进。”
《西长城》里俯拾皆是大时代下小人物的命运,书中也试图捕捉这一代兵团人的喜怒哀乐中所包含的共同的精神支撑,即兵团精神。不止一个被采访人说:如果没有谁谁谁,我早就没命了,哪里还有今天?跟战争的苦比起来,今天的苦算什么?这种劫后余生的幸运和感恩铸就了兵团战士毫无保留的牺牲精神,以及由这种牺牲精神而衍生出来的荣誉意识、集体意识、大局意识,久而久之,这种精神和意识就转化成了信仰。
是的,讲述新疆兵团历史的《西长城》就是一本关于信仰的书,也是一本关于生命的书,是一本生命与信仰血肉相连的、苍茫阔达的书。托尔斯泰说:“信仰就是生命。”而对兵团人来说,信仰帮助他们战胜恐惧和困苦,支撑他们的内心。信仰是时代永恒发展、历史永恒轮回的精神底蕴,甚至,它是历史的各种淘洗和时代的各种筛选中唯一能够留下来的真实。
作者在后记《乡关何处》中说:拓荒者用倒下的身躯唤醒了荒原,用一生的血汗滋养了戈壁,“老兵不死,他们只是慢慢离开……”当文学记录下这些无名英雄离开的时候,他们已经和丝绸之路、和林公车、和左公柳、和艾青的诗一起,变成了新疆故事不可分割的文化组成部分,而这些故事是我们共同的文化积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