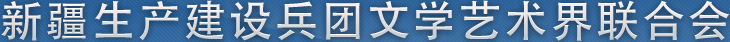地名是游子回家的路标,地名是连接历史的桥梁。
如果要在六师几百个连队地名中,选出文化含量高的前三名,我的排序是:唐南村(一○二团七连)、新渠城子村(一○三团十二连)、赵家村(新湖农场二十二连)。
上世纪80年代初,团场地名普查时,我在六师一○二团机关工作。说是普查,其实是给团场连队的驻地取名。多亏取名及时,避免了因连队合并带来的地名混乱。就像这个唐南村,最早是十八连,后来叫九连,现在是七连,而且团场之间大多是相同的连队番号。地名如此雷同,归乡的游子还能找到回家的路吗?可见给连队的驻地命名是必要也是必需的,不管连队名称怎样变化,地名不会变,唐南村还是唐南村。
好,还是说地名普查的事。那天晚上,机关开会研究连队命名的上报方案,各科室领导参加。团机关那时还在一个四合院的土坯房里办公,一间不算大的会议室,朦胧而昏暗。主持人一手拿着上报材料,一手还夹了一根点着的烟。当他读到十八连的唐南村时,打了一个磕,竟结巴起来。不知道他是不是觉得这个地名有点拗口,不像那些什么黄土沟呀、大疙瘩呀、沙槽子呀、大平滩那么顺嘴,那么有底气。他深深地吸了一口烟,那烟头在不太明亮的灯光下猛地一亮。我当时心血来潮,竟然大喊“唐南村这个地名好呀”,惹得那些科长们转过身来看我,他们或许觉得这有什么值得大呼小叫的呢?叫什么名不都一样吗?还能影响种粮食种棉花?
好在,所有命名全部通过。我唐突的大声称赞,没有产生任何不好的影响。
我当时也说不出不叫唐南村的地名有什么不好,只是听到在唐朝路之南的十八连取名“唐南村”时,马上联想到唐朝路(丝绸之路北道)上的商旅驼队,联想到大唐西域的兴盛繁荣,联想到北庭都护府旌旗飘动歌舞升平,联想到大诗人李白岑参,联想到“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诗句……好像给了一个超越时空的链接,马上有种“忽如故人心上过”的久违的温暖。顿时,我对那个边远的十八连、那个取出这么有文化底蕴地名的十八连人,心生敬畏之情。
十八连这个地方是一○二团最北面的连队,1960年才开荒创建的。我第一次到这里大概是1963年。那时,我当统计员。团场统计工作大检查,每人骑辆自行车,全场5个分场跑个遍,到十八连有近20公里的行程,还真是有点费劲。那时我年轻,才20来岁,到了十八连才知道新老连队的差距:路不平,晒死人,地窝子,灯不明。路过一、二、三分场还能断断续续地在林荫下骑车,一到四分场就是光秃秃的条田,没有一棵树,有林带的地也是刚栽的小树苗。十八连人好客,倒出的茶水都加了糖,但仍有又腥又苦的怪味。第二次大检查是夏末,自行车骑累了就到高高的玉米地葵花地边上休息片刻。在这么艰苦的环境中工作的十八连人,仍惦记着连队北面红柳丛中那条蜿蜒的古道,不失时机地在地名普查时,让它作为地名留传后世,贯通千年的文化血脉。
地名普查之后不久,我就调离了这个团场,新世纪之初,我参加了一个旅游文化资源考察组,在酝酿线路时,我马上提出一○二团十八连北面有条唐朝路。于是,我有机会近距离接触那条神秘的古道。
那天,当时的一○二团副团长钱士南陪我们去唐朝路。之后,我在《寻踪唐朝路》那篇文章中写道:
“汽车驶出连队的田野,在长满红柳梭梭的沙丘之间走了十几分钟。钱副团长说,唐朝路就在这片地方。唐朝路东起吉木萨尔的北庭,沿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南缘,经精河、伊犁到碎叶(唐朝诗人李白的诞生地,今吉尔吉斯斯坦的托克马克)与丝绸之路中线汇合通往中亚、西亚,又称碎叶路。
我们下车在沙窝里四处辨认,除了牲畜和野兽的蹄印就是偶尔留下的车辙,看不见史书上记载的那条宽阔平坦、路面铺设青泥的唐朝路。踏在脚下的是呈波纹状的沙质地面,软绵绵的,一步一个脚印。两旁是时而稀疏时而稠密的沙生灌木和杂草,不时有沙鸡从草丛中惊叫着飞跑出来。有一种能够站立的沙鼠整齐地立在洞口,向四周观望,当你走到跟前时,它敏捷地钻回洞里,洞口留下的是嚼碎的草梗。才翻了一个沙包,鞋口里已灌满沙土,手背上脖子上不知什么时候被铃铛刺划出了血痕。这里虽然离垦区不远,却好似走进一个与世隔绝的世界,让人体味到沙漠行路的艰辛。
又翻过一个沙包,在一片被水浸漫过的地方,终于看见了露出沙土的灰青色的路面。剥去表面的沙层,路面还是硬邦邦的,大概有四五米宽,像是被反复压过。在被水冲刷成断面的地方,路基下有一层已经炭化的树枝,可能是这段路地势较低,用以防止路面下沉吧。虽然路段大多被沙土掩埋,但仍可辨认出时隐时现的路迹。青色路面横穿丘垅,向东西延伸。钱副团长说,前些年,十七连、十八连的马车还能在这条路上跑。别看它简陋,走在上面晴天不起灰,雨天不起泥……”
2010年,唐南村那个地方划入工业园区,兴建起大型工业企业。唐代的武则天肯定想不到,在她下诏修建的唐朝路边竟然会出现一座钢城;当年的军垦战士也想不到,生产小麦玉米的沙窝边上也能生产钢材铝锭。那些连队子弟,则放下铁锹坎土曼、穿上工作服兴高采烈地到宽敞的车间里当了工人。
还有一个在十八连青年排工作过的团场子弟,2007年担任了国家某部副部长;还有一位出生在原八连(同处唐朝路南)职工的女儿李眉,如今是北京的职业作家,出版了《红颜沧桑》《火烈鸟》《北漂小姐》《年年槐花香》等多部中长篇小说,2017年上映了她编剧的电影《惊门》,作品得益于唐朝路的眷顾,还有地窝子、涝坝水的历练。
一千多年前的李白肯定是走过唐朝路的,不然写不出“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那样身临其境的诗句;如果李白走的是丝绸之路南道或中道,那只能是明月出昆仑了。假设一千多年前的李白穿越时空,再走唐朝路,驻足唐南村,看见天山脚下钢花飞溅、火树银花的壮丽景象,诗人该写出何等气魄的诗句呢?
不管岁月走多久,不管脚步走多远,故乡的游子都会记住这个地名:唐南村。而那一望无际曾经盛开的金灿灿的葵花地,那父辈们锃亮的铁锹和流着汗珠的肩膀,那地窝子里用红柳枝搭建的课桌,那沙包上抬起前腿站立在洞口机警地四处张望的沙鼠,那跨越千年已经被梭梭红柳遮掩的唐朝路……无论官员还是作家,无论是普通劳动者还是退休老人,这些,都是他们的乡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