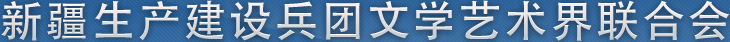“顶一下,错开,再顶一下,再让开。”
这是一个就算是长大了,偶尔还会做,且做了无数次的梦。梦里两个穿蓝布褂的男孩头凑在一起,胳膊也举在一起,拳头对拳头,抿着嘴,眼睛紧盯弯曲的食指,顶一下,擦过,再顶一下。
要说那个年代没什么玩的,这话不对,顶呱呱牛就是一项让人着魔的玩技。那会儿该多大?能把食指套在呱呱牛里,勾实了,和指头严丝合缝地勾实,那年纪应该是上学之前,最晚也就上了小学没两年,长太大,指头套不进去,太小了没顶牛的心劲。那时男孩间兴顶呱呱牛。书包里,口袋里会有不少呱呱牛。
能上阵顶的呱呱牛都是死牛,因为死牛壳硬。死牛不仅要死,而且还要埋在干土里,埋的时间越长壳就越硬。大院有两处符合要求的土墙,一处是果园的围墙,一处是大院的院墙。有段时间,我成天溜在那两截土墙边找呱呱牛,看到有露头的白点,我就会用指甲去抠。等我指甲都快劈的时候,我终于扣出一个顶级牛。那家伙天庭饱满,皮白而厚实,暗纹旋钮般地向上,曲线依次收紧,力道几乎全都集中在那最高的尖位上。
我认定每个呱呱牛都有自己的主人。我套着那只呱呱牛睡觉,做梦顶牛,梦醒,看看,再入梦。梦里把那两个家伙干掉无数回。要么就是盼望下大雨,下了大雨后围墙表面就会变软,藏在里面的呱呱牛就容易露头,还真的有几次呱呱牛露出头来朝我眨眼。
和人顶牛时我更是用心,顶之前先看对方拿出来的牛,对付那种傻白傻白的大个牛,你只需挑一个小一点但皮色发黄的牛收拾它就好。而如果对方拿出的同样是皮厚耐扛的家伙,那你就得小心了,如果双方拿出的呱呱牛品相相当,那就胜在顶牛时的巧劲上。头尖相对的瞬间让一下,只需错过对方冲过来的蛮劲,然后转手取道对手牛的薄弱点,手腕一挑就行了。
每战一次我都会吸取教训,积累经验。
有一阵,我终于成了班里玩呱呱牛的王。这是我年少时为数不多的荣耀。那只呱呱牛陪我好一阵时间,杀过无数败将,直到败在一个劲敌身上。我用红墨水点了它那顶塌的尖头,收进小箱里。我又开始寻找大杀器。
那天红脸蛋塔斯江骑马回来,见了我,他胳膊一伸,掌心摊开,我大叫一声,眼珠立马直了,他手里有一把呱呱牛!那些牛个个体格强壮,螺旋纹一圈圈盘上来,一切指标全都恰到好处。
我问他从哪儿挖来的,他说在河坝。于是我快快地拉着他,跑去河坝。
从县城向南直下,过了四道圈后就到了河坝。这段河滩宽阔散漫,中间是主流,两边是些分汊,即便在丰水季也到处看得见鹅卵石。说是河坝其实没坝,对岸是自然的缓坡丘陵,只在靠县城这边是一条自然形成的陡崖,崖下水流湍急。崖上倒是平坦,沿河岸看去是稀稀拉拉的蒿草,其间点缀着一丛丛马兰花。
那崖如今还在,却一点也不伟岸,这实在印证了一个道理:小时候看什么都大,长大后再回头看什么都小。我清楚地记得塔斯江带我走过一丛丛马兰花,快到崖边时,我只能停步,站在离崖边一两尺远的地方,听着崖下哗哗的水声。
“停下!”我说。塔斯江不解地转过身来。
“别,别下了,你会掉下去的。”我话中带喘,他皱起眉头,转身继续向前走。我绝不相信这是真的,眼前这个和我一般大的家伙怎么敢就这样下去找呱呱牛。
“喂!停下!”我吓得大叫起来。
哧溜一下,身子贴紧土崖滑下去,带起一溜崖上的土疙瘩,还没等我张大嘴,塔斯江踮着脚尖站住了,如果不是他喊呱呱牛,我绝不会挪到崖边向下看。现在我看清了,其实那崖并不是直上直下,崖下一人多深处,风化的碎石崖土堆积起一个小斜坡。塔斯江斜身靠崖,脚踩进说硬又软的土里,保持着身体平衡。
“下来看,这里都是牛将,你自己挖。”他说,顺手从碎土里捡起一个,用力一扔,呱呱牛划了道弧线飞了上来。
那天,我从塔斯江找来的一堆牛里挑出几只,去迎战。那段时间我打遍全校无敌手。谁都知道有这么一个大眼睛的家伙,顶呱呱牛没人能比。
终于有人得到了秘密,于是那河坝边的陡崖成了呱呱牛爱好者的去处。
那最后一只呱呱牛从此就一直藏在我的百宝箱里,我再没拿它去寻找对手。那以后我渐渐长大,玩耍的圈子里已没人再玩顶牛。它也就只剩孤独求败的自己,只剩我在梦里和自己玩,从一定意义上讲,它早已没了对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