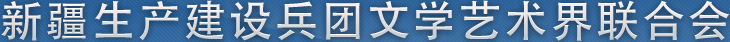“你个小机灵,精得很!”关凤莲阿姨带着浓重的中原口音笑着对我说。
30多年过去了,想起第一次见到阿姨的情景,恍若昨天。关凤莲阿姨是我二嫂的母亲,她老人家的小儿子聂卫阳也是我最好的发小。每次想起阿姨,我不由自主想起那一盆一盆的粽子。
和很多团场人的家庭组成一样,男主人和女主人来自不同的省份,我的父母一个是四川人一个是陕西人,这是兵团“五湖四海”的最好证明。这也使兵团的文化极具包容性,而最直接的体现恐怕非饮食文化莫属。在我的记忆里,家里开始吃粽子,大概是上世纪80年代初,在这之前,究竟是因为父母都不会包粽子,还是因为贫困的年代物资匮乏所致,不得而知。
二嫂娘家是从三连调到园林二连来的。记得刚搬来的第一年秋天,大人们都在地里收打瓜,我们小孩子也过去凑热闹。想不起来当时是说起什么话题,就发生了文章开头的一幕。后来慢慢熟悉了,我才渐渐回过味来:阿姨这是在夸我啊!
其时刚改革开放不久,团场正逐步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我们这一连人,大多是“文革”中被“发配”到远在山沟沟里的四师六十一团煤矿,刚刚落实了政策整体搬迁回来的“牛鬼蛇神”。父亲由原来的副矿长改任副连长,二嫂的父亲聂成甲调任政治指导员,由于工作关系,两家的走动自然多了起来。
关凤莲阿姨人缘很好,每逢端午她不仅自己包粽子,她三连的老邻居还会让孩子把煮熟的粽子大老远送到园林二连来,老人家必定会给我们家端一盆过来,这时候我就能美美吃上几天。因为粽子,我和老人家的干儿子小蛋蛋,小蛋蛋的哥哥大蛋蛋以及老邻居家的黄狗、花狗两兄弟都成了朋友。一转眼,我离开六十一团快30年了,当年的小朋友也都应该是两鬓斑白了,他们儿时的模样,还时时浮现在眼前。
可以说,华夏大地,没有哪一种美食和文化无关,粽子则更具代表性。据说端午节吃粽子最早起源于荆楚大地,是为了纪念爱国诗人屈原,随后慢慢演变成一个节日,赛龙舟、点雄黄、折艾叶、戴香囊、悬菖蒲成为江南水乡的习俗,无一不透露出美好的祈愿。后来想想,粽子是水稻文化圈的产物,新疆干旱少雨,早年是小麦玉米的天下,本地人不会包粽子也情有可原。后来,来自五湖四海的兵团人,为了改良伊犁河边的盐碱滩,把内地的水稻种植技术“嫁接”到了塞外江南,造就了西部边陲的鱼米之乡,粽子也就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人们的餐桌上。如今每逢传统节日,很多幼儿园和学校都会举办相应的国学知识讲座和趣味活动,对传承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颇有影响。
父母退休后有了时间也慢慢学会了包粽子,虽然手法不似来自江南水乡的老职工那么娴熟,能够灵巧地把芦苇叶穿过粽身一次成型。父亲和母亲包的粽子,都是用做缝纫的白线绳扎捆,虽不美观,内容却很扎实,圆滚滚的身子里满满的米和红枣。上世纪80年代初,生活刚有起色,大家手头都不宽裕,刚从“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日子里走出来的人们,依旧保持着节俭的本色。就拿包粽子来说,连队人家通用的做法大多是一半大米、一半糯米,因为大米的价格比糯米便宜些。吃红枣粽子要蘸白砂糖,可是那时候谁家有钱买这样精贵的佐料呢?刚好师里新建了霍尔果斯糖厂,每年秋冬季节,马路上一车一车的甜菜(我们叫作糖萝卜)源源不断地送往那里,由于路况不好,运输车在坑坑洼洼的马路上扭秧歌似的前行,免不了会有一些糖萝卜掉落路边。这是我们最快乐的时候。作为一个新建的园林连队,我们的父辈只能在戈壁滩见缝插针开垦土地栽植果树,糖萝卜是拥有大片土地的农业连队才能种植的新作物,我们自然只有眼馋的份儿。因为离学校远,冬天我们大多是头顶着星星和月亮出门,偶尔发现几个白白胖胖的糖萝卜躺在路边,我们会大喜过望,立即捡起来藏在路边的隐蔽处,等下午放学回来时再带回家。大人们则把糖萝卜切成条,放在水里煮熟,然后用慢火熬成黑红色的糖浆(我们俗称为糖稀),无论是吃粽子,还是蘸馒头,都别有风味,我感觉比正宗的白砂糖还要好吃。水煮过的糖萝卜条,不仅能当水果吃,而且还顶饿,也很受我们的欢迎。
记得父母第一次包粽子,包了满满一大盆,大小参差不齐,出锅后,我迫不及待地剥开一个就想下咽,却迅速吐了出来,原来粽子竟然没有煮熟,还是夹生的。向南方人求教,才知道是因为泡米和水煮的时间都不够,这个经历让我们开心地说笑了好些年。由于父母爱吃粽子,工作后为了让两位老人省事些,我常常买了包装精美的粽子送回去。这些粽子虽然花式繁多,但总觉得缺了点什么。
有一次我回到家,父母已买回新鲜的糯米,包了一盆粽子,这时候母亲已经不再放普通大米了。剥开苇叶,一股清香扑鼻而来,一口下去,更是从味蕾到心灵的满足,我这才明白超市的粽子究竟缺了什么。从此,我不再买超市的粽子回家,而是给父母买当季的糯米和红枣,而且一定按母亲的嘱咐,买那种圆圆胖胖的糯米,这种糯米比外形细长的糯米更适合包粽子。
岳父岳母都是浙江人,对包粽子颇有心得,这也让我对粽子有了新的认识:原来除了糯米红枣,粽子还有这么多吃法,有鲜肉、酱肉、板栗、火腿、蛋黄、豆沙、莲子……凡可入菜者,皆可包粽子,咸甜酸辣随心所欲。而粽子的形状,除了我之前常见的三角形,还有正四角形、五角形、方形、长条形等,这真是令我大开眼界。岳父还说,当年连队的温州支青把包好的粽子浸在稻草灰调和汤水中浸泡数十小时,再用汤水将粽子煮烂,不仅吃起来满口稻草的清香味,而且在常温条件下存放半个月不变质,真是美味的干粮。
由于这种渊源,这些年出差江浙,我对粽子情有独钟,即使在高速路的休息站,我也忍不住会买几个用电饭煲热着的粽子大快朵颐。游览乌镇,看到一所所民居虽已成为景点,但是几乎家家的院门上都不忘挂一串菖蒲或者几片艾叶,不禁为传统文化的延续感到欣慰。前年休假去嘉兴拜谒红色革命的发源地,我专程去品味赫赫有名的五芳斋粽子,算是对粽子文化的尊重。顺道去景德镇看望妻姐,吃了一种类似炒年糕的碱水粑粑,入口筋道,回味无穷,追溯历史竟然也是从一种类似粽子的碱水果子演变而来。粽子真是无处不在。
工作后在伊宁市居住了20多年,上世纪90年代,常见回族妇女的手推车上,煮熟的粽子配以黄色的佐料,最初以为是蜂蜜,吃着又感觉风味独特,和蜂蜜略有区别。这个疑惑在心里盘旋了很久,直到前几年看到一篇介绍伊宁市汉人街的文章,才知道这种佐料是回族手艺人的独创:选用上等黄小米、黄萝卜为主料,精心熬制的糖稀。难怪当年品味时感觉似蜂蜜而又比蜂蜜多了些味道,甜中带着酸,让味蕾多了些体验。只是可惜,随着城市建设和管理的日益规范,街边摊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当年随处可见的街头美食也杳如黄鹤,高档的酒店宾馆虽有价格不菲的各式粽子,却吃不出岁月的味道。
转眼又要到端午节了,我却离开了伊犁,离开了亲人,独自面对新的环境新的挑战,这时候多想再听一声关凤莲阿姨的中原口音,多想再回家美美地睡一觉,然后大口吃着母亲刚从锅里捞出来的热气腾腾的红枣粽子啊!
这是母亲离去的第一个端午节,想着她的音容笑貌,稻米的清香似乎从心中漫延开来,眼角渐渐湿润起来。